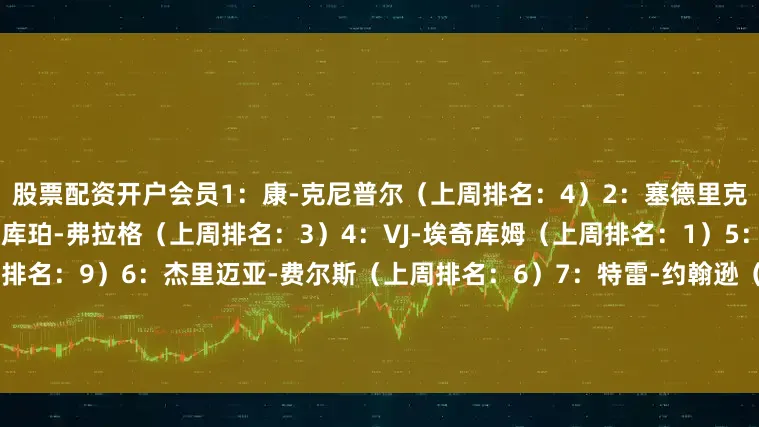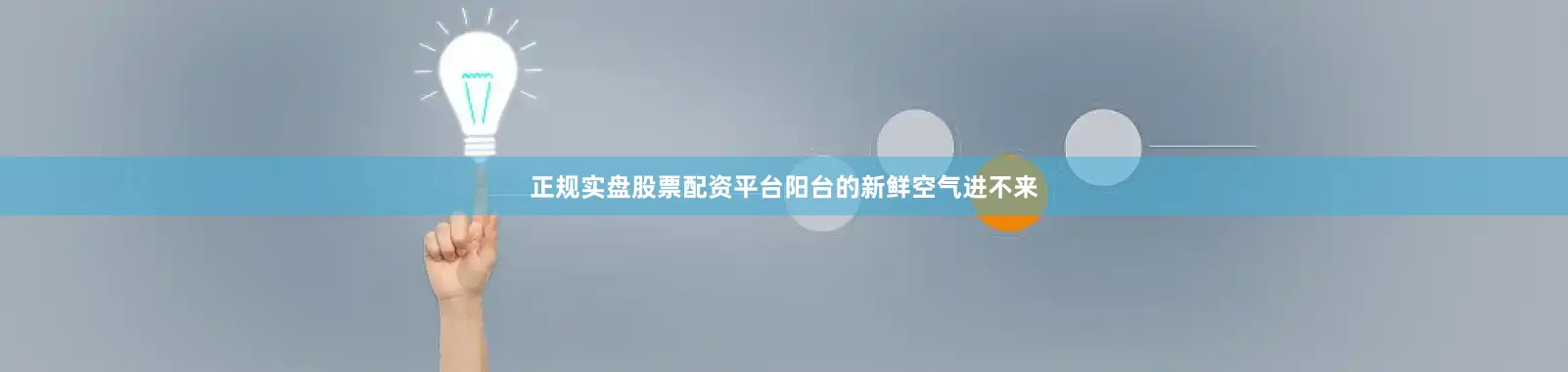《脾胃论》的第七章“用药宜禁论”,是个典型的“总-分-总”结构。
东垣第一句话就交代说,本章的内容围绕着四大“禁”:时禁、经禁、病禁、药禁。随后用了四段文字,分别针对四禁。章节的最后一句,又带着读者重新快速回顾了四禁,“察其时,辨其经,审其病,而后用药”,并再次强调说,若能谨守“时、经、病、药”之禁,问题就不大了,“四者不失其宜,则善矣”。
【第一禁:时禁】
我们来看看李东垣说了哪些时禁,他提出这些时禁,其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?
“夫时禁者,必本四时升降之理。”
在第五章的“君臣佐使法”里,东垣便同样提醒过:“凡药之所用,皆以气味为主,补泻在味,随时换气”。
他笔下的“随时”,可不是我们现在的意思,而是随时间随季节随天地之气变化的意思。
“随时”调整的理念,大约到了明中期以后就变得非常淡漠了。到了清代医家的医案里,更是几乎看不到什么影子了。而我们若是读李东垣,会发现这个概念无处不在,遍布他医书里每一页的文字中。这种反差感,你若真有观察到体会到,刚开始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撼。
咱上一篇介绍《五积门》,东垣在其每个方子后面,都说明了天冷天暖的加减宗旨。总体而言,正如他治“厥气”表示要加吴茱萸,但紧接着又补充说若是天气大热时出现同样的症状,则须改用黄连黄柏知母酒制为丸那样,天暖减热药或再加寒药,天冷减寒药或再加热药。
因为同样的症状,比如同为气逆,其“卫气状态”是不同的。冬天由于外寒束表,导致卫气更偏于沉位,也就是稽留得更为严重,一般而言。
是否还记得《内经》里所说的“故春气在经脉;夏气在孙络;长夏气在肌肉;秋气在皮肤;冬气在骨髓中”,“春气在毫毛,夏气在皮肤,秋气在分肉,冬气在筋骨”等,古人说的正是随天地之气的升降沉浮,卫气在体表区域所对应的升降沉浮。
你可以想象“卫气状态”图,随春夏秋冬而变大变小。一年中最热时,圈子最大;一年中最冷时,圈子最小。而之所以用药须对应时节变化,其本质是为了正确地顾及到“卫气线”的状态。或是加药以弥补变小的圈子,或是减药以避免加重圈子缩小;或是可将重点放在解决阴火问题上,而仅稍顾及卫气线…等等。
所有“随时”的加减,都是为了避免“太过”或“不及”,升之不及,升之太过,降之不及,降之太过。
如果说东垣在消食法与“五积门”里,强调“随时”是为了着重于,药味之寒热的择用,须对应两线的具体格局,那么他在本章的“时禁”内容里,则又对其进行了扩展。
“汗、下、吐、利之宜。大法春宜吐,象万物之发生,耕耨科斫,使阳气之郁者易达也。夏宜汗,象万物之浮而有余也。秋宜下,象万物之收成,推陈致新,而使阳气易收也。冬周密,象万物之闭藏,使阳气不动也。”
东垣想要说的是啥意思哈?
借势~!
古代大医家们都非常擅长“借势”。
是否还记得张子和挑了一个大晴天,去给病人中风后遗留的麻木手指进行针刺治疗?参《张子和的外治法之针灸法》
是否还记得张子和又挑了一个大晴天,还是大中午,给一位喉痹的患者,进行小口频服滚烫的苦寒药的治疗?参《金元明清医家们使用噙化法的治案》
是否还记得李东垣在某年农历六月间治疗手指麻木三年未愈的病人,先用内服药将其病势推到了手指末端,再进行刺络放血的治疗?参《三年麻木,三天除去!丨东垣医案19》
又是否还记得喻嘉言对痰结的病人说,在多少天后的立冬日便能决一胜负?参《喻嘉言是怎么治痰结胸膈的》
正如上文所说的,古人非常清楚人体气机会随天地之气而升降沉浮。因而,在面对疾病须如何处理如何选择适当的出路时,便会一并将天时给考虑进去。
于是,就有了充满智慧的“借势”~!
因为,顺势而为,往往事半而功倍;逆势妄为,则必然事倍且无功。
“经云:夫四时阴阳者,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,逆其根,伐其本,坏其真矣。”
违背天地之升降沉浮,即“四时阴阳”,照李东垣的意思是,不仅仅只是无功,而是破坏性极大。
以上说的是,医者要能顺应“时势”,懂得“借势”而为。
那么紧接着的后一句,怎么乍看起来似乎又与之相反啊?
“又云:用温远温,用热远热,用凉远凉,用寒远寒,无翼其胜也。”
我们后人其实大多对这句话更为熟悉,因为每本基础教材里每年的考题里都有。
意思是,天热时勿用大热药,天寒时勿用大寒药。
那和上文所说的,天热时用达表的吐汗法,天寒时用降行的利下法,似乎看起来说法互相违背啊?
其实,两者的出发点一致,只是所指的角度不同而已。
我们刚才说了,“随时”调整的本质,是要确保做到,既不“太过”亦不“不及”,无论升降,无论两线,皆是如此。
那么,当病人升之不及,而我们又必须选用达表法时,天时之升就刚好为我们提供了最完美的助力;当病人降之不及,而我们又必须选用利下法时,天时之降就也刚好为我们提供了最完美的助力。
以上就是:借势~~~!
但是,当病人升之太过,而天时又偏于升浮时,我们就不能再用药去火上浇油了;当病人降之太过,而天时又偏于降沉时,我们就不能再用药去雪上加霜了。
以上就是:用X远X~~~!
可能有读者看出来了,【病人、天时、用药】,三者之间必须共同达成两线的平衡。
①当【病人+用药】,仍稍稍偏于“不足”时,若刚好能借【天时】来弥补“不足”,我们应该学会主动去借势来用;②当【病人+天时】,已经形成“太过”时,那我们的【用药】就不能仅仅只考虑到病人的情况,还要将天时也一并考虑进去,来进行适当的矫正。
所以刚才会说,东垣的两个说法都对,只是角度不同。
“故冬不用白虎,夏不用青龙,春夏不服桂枝”,说的是②的情况,不能用药更助太过或不足;“如春夏而下,秋冬而汗,是失天信,伐天和也”,“秋冬不服麻黄”,说的是①的反面,未能顺势而为,反而逆势妄为。
不过顶尖的医家都具有一个常人很难习得的禀赋,便是“灵活”,而灵活的最高境界正是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。
李东垣正是这么一位顶尖的医家,所以他在“时禁”一段的最后,又补充说了一句:“有病则从权,过则更之。”
我以前说过,“从权”或其近义词,是李东垣最常写到的关键词汇。我们能从中看出他非同一般的智慧与善巧,实非刻板死板泥于规矩表面而不悟底层规律之人,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。
任何规则,本质都是为了正确更好地做事儿。所以,无论是恪守古人所说的在对应的时节使用汗吐下法以及用X远X,还是看似不按古训未在对应时节使用汗吐下法或未用X远X,实则都是为了以正确的手段取得最好的结果。
我们在读医案时,常常会读到诸多前医或看客,将古训背得滚瓜烂熟,对于主角医家的治法,指手画脚指点江山,每每试图以前贤之语来证明主角是错的,结果当然是哑巴吃黄连咯。
不过作为读者我们要能明白,并不是这些看客所背的古训有问题。正如最近在进行解读的《伤寒论》一样,古人常常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医理。我们要能懂得他们的意图,看到他们所指的不同角度,而不困于看似相违的表面。
【第二禁:经禁】
本段文字东垣依次介绍了三阳三阴的主要治法规则。
同样要观察的是,当东垣在说“经禁”的时候,他背后想要强调的本质又是什么?
“足太阳膀胱经为诸阳之首,行于背,表之表,风寒所伤则宜汗。”
足太阳位于人体最表层,因而,当足太阳经脉之气因受外寒而通行不利时,首先应该使用表散法发汗法。
说其为发汗法,其实本质仍是用药将气血调动到体表之足太阳膀胱经。以善行膀胱经经气之药味,来恢复该经脉的通行。由于经气重新畅行,即卫气恢复外达,则阴火随之外解而汗出。
当以卫气线不升为主要矛盾时,不能主以降行法。否则,会进一步困遏卫气线,加重卫气稽留,从而引发诸多后续问题,“若下之太早,必变证百出,此一禁也。”
“传入本则宜利小便。”
除非,病势已经传到了膀胱腑,即以小便不利为主要矛盾,那就应当使用利小便法。
“足阳明胃经,行身之前,主腹满胀,大便难,宜下之,盖阳明化燥火,津液不能停,禁发汗、利小便,为重损津液,此二禁也。”
足阳明胃经经脉的路线主要在身之前侧,因而,当足阳明经气不利时,往往会出现腹部胀满,大便难的情况。此时,应当解决大肠腑的积滞问题,而不该使用发汗法或利小便法。后者纯属杀敌为零自损亿万。
以上足太阳足阳明的内容,可与《伤寒论》“两线解“的【035】条互参。
“足少阳胆经,行身之侧,在太阳、阳明之间,病则往来寒热,口苦胸胁痛。”
足少阳经脉之所行,主要在身体的侧面,在太阳与阳明之间。足太阳多恶寒,足阳明多恶热。因足少阳经脉位置的特点,当其经气不利时,最常出现的表现就是往来寒热,以及经脉所过之处因两线之争而出现诸多不适。
“只宜和解。且胆者、无出无入,又主发生之气,下则犯太阳,汗则犯阳明,利小便则使生发之气反陷入阴中,此三禁也。”
首先是因为足少阳位于两者之间,既不能像足太阳那样使用发汗法(伤及阳明),亦不能像足阳明那样使用通下法(伤及太阳)。其次,其特定的生理结构特点(无出入),与其主生发的特性,都决定了其不适合使用下法,会导致“生发之气反陷入阴中”,即严重困遏卫气线。
“三阴非胃实不当下,为三阴无传本,须胃实得下也。分经用药,有所据焉。”
三阴经不像足太阳那样有“传本”之膀胱腑(前阴)、足阳明那样本身就会传到大肠腑(后阴),因此只有当三阴经脉通行不利的病势已经波及到了胃肠,且出现了胃肠实积,才可使用下法,否则也不应当径用下法。
“分经用药,有所据焉。”
李东垣提醒读者,要严格根据病势波及的经脉,来选择合适的治法。
综上,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下本段开头的那个问题:
东垣强调“经禁”其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?
势在表的,从表走;势在里的,从里下;势在中的,用和解;本身无有出路,且主生发的,不应使用通利法;但本身虽无有出路,若是病势已波及到膀胱腑大肠腑,则可使用利小便法通下法,等等。
是不是仍然围绕着,治法须谨守“升降沉浮”之势?或是顺势借势,或是不逆势妄为。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兼顾两线,既解决阴火问题,亦不误伤及卫气。
【第三禁:病禁】
说是“病禁”,其内容主要就是“饮食口味”之禁。本段可与本系列的《东垣笔下典型的味与脉丨《解构脾胃论》11》互参。
“病禁者,如阳气不足,阴气有余之病,则凡饮食及药,忌助阴泻阳。”
大法,对于本身已经病于升之不及者,不得再以饮食或药味,加重升之不及。
这里的“阳气不足,阴气有余”,仍是《内经》里“阳气少阴气多”的意思,直接理解为“升之不及”。
“诸淡食及淡味之药,泻升发以助收敛也,诸苦药皆沉,泻阳气之散浮”;“生、冷、硬物损阳气,皆所当禁也”。
之前说过,“淡”在这里不是清淡的意思,而是淡渗的意思。中药主淡渗的,皆为降行药。东垣所说的“泻升发”“泻阳气之散浮”,即是“泻阳”的意思;“助收敛”,即是“助降行”的意思。
本证应当“助升发”“助阳”,“泻收敛”“泻阴”,而“忌助阴泻阳”,所以不得误用淡渗、苦药、生冷硬物。
但你以为东垣是想要鼓励你多多使用辛热么?
绝对不是~!
“诸姜、附、官桂辛热之药,及湿面、酒、大料物之类,助火而泻元气。”
这些辛热之味,并不能助元气,反而是助阴火泻元气。
我一直在说,这是东垣被后世误解最多的地方。他从来都是提醒读者,莫要误用过用辛味,以免重伤元气。
“如阴火欲衰而退,以三焦元气未盛,必口淡淡,如咸物亦所当禁。”
上一篇文章刚提到“咸”味的禁忌,东垣治各种“结”极少用到典型的咸味软坚药,他治下焦各种漏下病也极少用,是因为他非常清楚,气液的异常疏泄,无论是聚而不散,还是行而不止,其本身都是“卫稽”的产物。用李东垣的话来说,是因阳道不行、气不升阳。
咸味固然有软坚的作用,但也会加重血脉凝滞(按《内经》说法);咸味固然有收涩的作用,但也会因其主降行而加重卫稽。
而所有问题得到真正改善的前提条件是,卫稽状态的整体改善。
所以,到底是整体解决两线问题,还是见X治X?
后者有可能一时解决症状,也有可能因加重卫稽而造成迁延或加重症状;但选择前者是需要强大的实力做为后盾的。
“病禁”或“味禁”这一段,说的其实还是“升降沉浮”的问题。东垣仍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,切莫加重“升之不及”。
【第四禁:药禁】
“药禁者,如胃气不行,内亡津液而干涸,求汤饮以自救,非渴也,乃口干也,非温胜也,乃血病也。”
这句话恐怕会有不少读者理解不了,那就先看最后一小句:“乃血病也”。
反推东垣的意思,是想说此口干欲饮,不是“气病”,不是气分大热,你可别误用凉药误伤及气啊~~~!
那这里的“血病”是后世温病学派所说的“血分证”么?
不是。
李东垣认为,阴火从一开始,就在血分中。参《从李东垣的风热方,看解决发热证的本质。|《解构脾胃论》19》。
在卫稽稽留的状态下,由于气血阴阳都会被阴火给异常的消耗掉;又因卫稽,各大经脉之通行外达难以有效开展,因此,气血阴阳物质又难以有效生成。
也就是,源&流,两头都重伤。
在这种情况下,不少病人会出现口干欲饮的情况,但大多其实喝不了太多水,有的索性只是欲饮,而不会真的去饮。
所以东垣想要提醒你的是,不要再误用凉药重伤元气。
那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?
升阳+泻阴火,这是《脾胃论》第三章整个章节反反复复围绕的内容,参《读明白“脾胃胜衰论”,才可能读明白《脾胃论》丨《解构脾胃论》12》。
“当以辛酸益之,而淡渗五苓之类,则所当禁也。”
辛,就是升阳;酸,就是泻阴火。但不要拘泥于“辛酸”二味哈,领会东垣想要表达的“升阳+泻阴火”的总治则即可。
“汗多禁利小便,小便多禁发汗。咽痛禁发汗利小便。若大便快利,不得更利。”
尽管不是因“气分大热”而津液不足,但也不能再肆意妄为重竭津液了。
“大便秘涩,以当归、桃仁、麻子仁、郁李仁、皂角仁,和血润肠,如燥药则所当禁者。吐多不得复吐。”
以上说的都是在津液不足的情况下,不得滥用大耗津液的治法,比如汗吐下法。
即便必须通便或必须使用吐法,也应当注意具体的操作手法。比如使用润肠的药味来通便,而不用燥药;又比如不得反复连续多次使用吐法。
“如吐而大便虚软者,此上气壅滞,以姜、橘之属宣之;吐而大便不通,则利大便,上药则所当禁也。诸病恶疮,及小儿癍后,大便实者,亦当下之,而姜、橘之类,则所当禁也。”
前面“三大禁”都围绕“升降沉浮”,且相对更侧重于其中的“升之不及”。我们读到第四禁时,是否会以为东垣改换了赛道,想写如何生津养液啦?
错了哈~~~这就不是李东垣了哈!
在提醒勿重伤津液,并例举在津液不足的情况下,如何正确通便之后,李东垣的本色很快又跳出来了~
估计是怕读者读了以后就只会使用通幽汤之类的润肠法了,他赶紧补上了几个不同的通便法。
以前在《从李东垣对十剂的补充,来品鉴他变态级别的周全》篇里,我曾重点介绍过这段内容。
用姜橘法针对的是上焦气滞,姜橘本质上仍是升阳达表法;用通利大便法针对的是胃肠积滞导致的大便不通,此法在瘟疫中用得较多,比如吴又可就最常提到。
而且,当应当使用通利法,比如温热疫病而大便闭塞时,你若使用降橘法或升阳达表法,就是错误的;反之,该达表时,用通下法,亦是错误的。这就是李东垣写的两个“所当禁”。
到了这里,是不是又和“第一禁”与“第二禁”的内容高度相似了?
再来~~~
“又如脉弦而服平胃散,脉缓而服黄芪建中汤,乃实实虚虚,皆所当禁也。”
在东垣笔下,“弦”即为卫气线不升,“缓”则为湿盛。因此,相对而言,前者属虚而后者属实。黄芪建中汤是李东垣的“老五方”之一,可视为典型的东垣方的前身,常用来处理卫气线不升的情况。而湿盛正未虚的情况下,则因以燥湿利湿为主。
因而,脉弦对应黄芪建中汤,脉缓对应平胃散。两者若是互换,就会造成“实实虚虚”的严重误治了。
“人禀天之湿化而生胃也,胃之与湿,其名虽二,其实一也。湿能滋养于胃,胃湿有余,亦当泻湿之太过也;胃之不足,惟湿物能滋养。仲景云:胃胜思汤饼,而胃虚食汤饼者,往往增剧,湿能助火,火旺郁而不通主大热。初病火旺不可食,以助火也。”
东垣这段话是在说“湿郁”。
胃喜润恶燥,适当的“湿”有利于胃气运行,但若是过度了,反而会成为负担。湿气过多,难化难散,则会积聚生热。其本质还是因阻碍了经脉之气的正常通行,而令经气陷入了【厥+逆】的状态。所生之热,即属逆象。
所以,助湿的饮食,亦会助火,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。
“病禁”是从“津液”的问题开始的,但东垣说此津液不足是因卫稽,也就是升之不及,治法则是升阳泻阴火;之后又紧随润肠法,说还有达表法与通下法来治大便不通,并强调两者不能用反;再之后,以老五方的黄芪建中汤与平胃散为例,提醒不能互相颠倒;最后以“湿郁化火”会助阴火来作为结尾。
可见,“病禁”仍是围绕着“升降沉浮”,围绕着“借势顺势”与“不得逆势”,围绕着不加重卫气线不升不更助阴火线不降,围绕着两线兼顾。
我们在本系列之前说过,东垣的一切药味加减法,皆为两线法,而本章的用药或宜或禁,亦是如此!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十大炒股杠杆平台排名,股票配资配资,十大实盘配资排行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